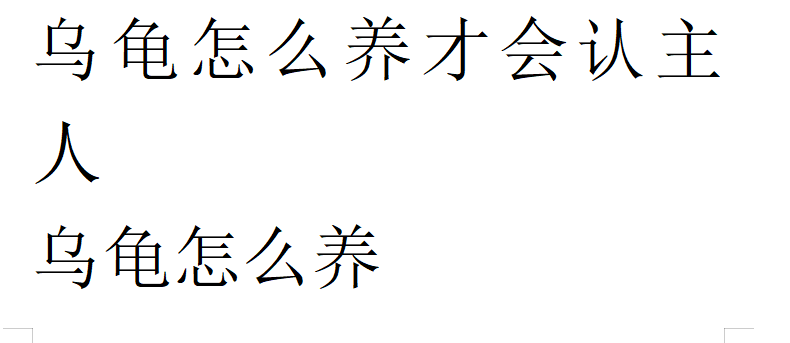童年印象里的甲鱼不怎么受待见。记得是齐云山周边的一个村子,过年前要起塘捉鱼。生产队长带着几个“后生仆”(方言,指年轻人),抬着水泵和长长的塑料管来到大水塘边。后生仆们拉线架泵,水管一头一头伸进塘里,另一头则被甩进板桥下的小溪里。
水泵一开,声音开始瓮声瓮气,继而高亢尖厉。抽了一会儿,原本静静的塘面上泛起了几圈漪涟,眼尖的看见几张鱼嘴贴着水面在呼吸。“啪”的一声,一条大鲤鱼跃出水面,又落了下去。鱼开始频频地越出水面,此起彼伏,鳞光闪闪。后生仆用网兜轻而易举地把一条条草鱼、鲢鱼、鲤鱼拿住,随手往人扎堆的地方摔。鱼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,落地了还蹦跳个不停,好几双手都按不住。
待到水干泥出时,就要用手在污泥里摸了。突然,翻出了一个圆圆扁扁的玩意,一挥手,像投掷铁饼一样,扔到岸边好远的草滩上。我们一大帮孩子蜂拥过去,一看,原来是只大甲鱼。它居然没有被摔死摔昏,正急急地往枯草丛里钻。一个孩子用树枝一拨,它便四脚朝天,任人摆布了。这家伙足足有三、四斤重,也不知在塘里养了几年。
那年月甲鱼卖不出价,宰杀起来也非常麻烦。队长不收归队有,孩子们欢天喜地,围成一圈变着法子玩,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。末了,村西头的明仂用一根细柳条枝绑扎了这只甲鱼,一步两晃地拎回家了。
其实,甲鱼曾经还是挺受追捧的。徽菜有两道菜很有名:雪天果子狸,沙地马蹄鳖。前者早就不准为菜了,后者倒时不时地在酒桌上被“一睹真容”。今非昔比了,区别在于家养而非野生。
我家附近有一家专做甲鱼的餐馆。一进门,就是几张甲鱼的大幅彩照,模样生动,好像要爬出画面了。也是明码标价的:水库价、水塘价、水池价。最贵的当然是水库价,一只甲鱼吃下来,得要几百块钱。伙计告诉我,这水库养出来的,几近野生的了,自然身价不菲了。我笑了:你这是按水面大小卖鳖了。
我可没在这家店里吃,一则甲鱼太大,耗糜银子;二则没有清炖的,皆为红烧,重油重色重料,红光闪亮。鄙人血压血脂偏高,受用不了呀!
首先是挑买甲鱼。父亲讲究,不仅要野生的,而且要上品。他的眼光挑剔,先看甲鱼的肚皮,得要有颜色发白的花斑;然后看四个爪子,要偏黄色,比较尖锐;再看背壳,要薄而发黑有光泽,裙边上翘宽厚。个头要斤把重的,父亲说,太大的有腥味,太小的就全是骨头了。当然,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。
如此,一年也就只品尝次把而已,一般是在春季。父亲是老中医,他知道此时的甲鱼营养价值高,最补。而且甲鱼经过一冬天的蛰伏静养,肉长得结实鲜嫩,十分可口。
宰杀甲鱼后,剁成十来块,得仔细地把甲鱼全身的乌黑污皮轻轻刮净,注意可别把裙边刮破,腿边的黄油也得拿掉。然后把甲鱼放进滚开水中焯几分钟,去掉腥味,置于一蓝边大碗里,甲鱼肉上,均匀地铺火腿十余片。火腿最好是陈年的,切得薄薄的,呈深红色。父亲说火腿片不宜过多,其咸香与甲鱼的生鲜相得益彰,亦可冲和后者残留的腥味。多了,就喧宾夺主了。最后放姜葱料酒。
大碗置于一大钢精锅里,放足水,在炭火炉上炖将起来。文火,内敛深沉,不动声色。一刻钟后,锅水沸腾,发出“咕咕”的欢快声;又一刻钟,热气从紧闭的锅盖边侧漏出,由厨房到正房,袅袅飘忽。甲鱼与火腿的混合香味形成一片氤氲,让人熏熏然。
炖一小时,大功告成。其滋味无需言表,每个家庭成员大抵分得甲鱼肉一块、火腿两片,尝尝而已,很不过瘾。
当下林林总总的徽菜里,臭鳜鱼、刀板香、毛豆腐似成三足鼎立之势。其实,一桌道地的徽菜宴,炖甲鱼还是压轴的,没有它,镇不住桌面。它上场形象完整,栩栩如生,但见清汤如许,四脚凫水(汤),背负暗红(火腿片)…。
约定俗成,甲鱼昂昂高抬的头总对着桌上年长或德高望重者。在众人的一再恭请下,他(更多时候是他人帮助)举箸揭开甲鱼背壳,收入碗里。于是大家开动,吃肉便吃肉,喝汤便喝汤。
新安晚报、安徽网、大皖新闻有奖征集新闻线索,可以是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形式,一经采用将给予奖励。
报料方式:新安晚报官方微信(id:xawbxawb),大皖新闻“报料”栏目,视频报料邮箱(),24小时新闻热线!
如文中采用图片无法联系上作者,请通过与本网联系,提供姓名、联系电话、银行卡号、开户行信息和地址,以便支付稿酬。